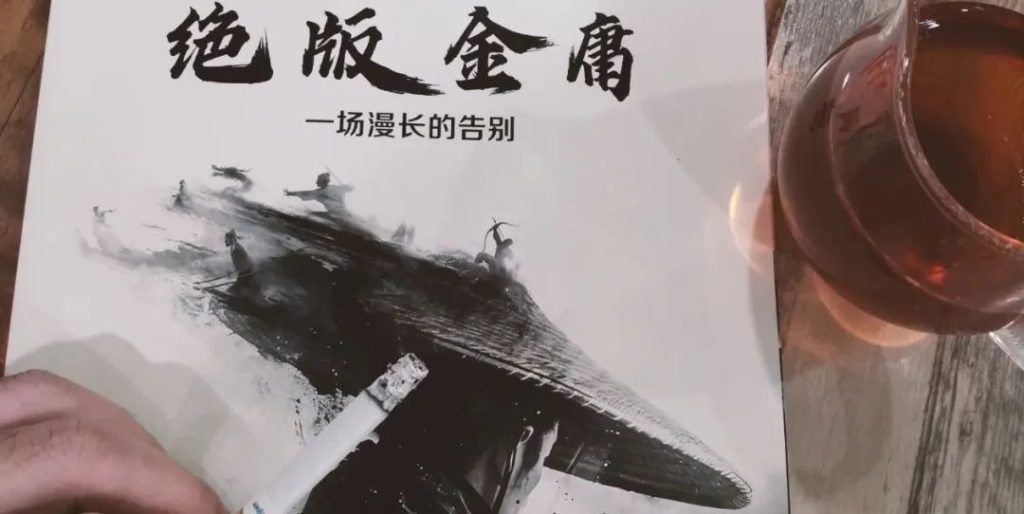一
有一时,就是智能手机风行的那几年,国内的几家银行的办事效率日见提升了。银行窗口前长队蜿蜒的风景淡出,银钱出入渐渐变作手机屏上浮动的数字。便连一向执迷于现钱的乡下人,也知这块薄薄的金属靠谱,很乐意使用。一时之间,无论老幼贫富,个个指尖翻飞。
久而久之,那支付软件更是化身为一方小小的“通行证”——乘车、购物、挂号、点餐,但凡生活中一点沟沟坎坎,非持它不能迈过。出门不带手机,不但行路难,连去街边小铺买只烧饼,也要挨店家的白眼。
前几日我因新机初装,自要逐一安放应用,却遇一道关隘:某软件竟索求读取相册中所有图片,未勾选“同意”则不允许安装。但手机里的相片属于隐私,被冒昧读取,不啻将我的裸照公之于众。被逼无奈,我一咬牙点击“同意”。瞬间,界面欢腾舒展,缤纷世界重新跃于掌上。便捷在手,终归令人心安。
某一夜睡前,暗室中荧屏幽幽亮起,无数图标如星河明灭。突然一念袭来,使我遍体生寒:这哪里是便捷?分明是数字时代重塑了权力运作的本质,以数据、算法与代码为载体,通过隐形技术架构运作,塑造个体偏好。我们将浑身内外每一寸空间典押给那冰冷的“通行证”,却因换取一点甘甜便自鸣得意。
从前要龙袍玉玺才撑得起的威权,如今竟靠“技术理性”四字便坐稳江山。你我贪图便利,闭眼签下隐私文书,却似俯首自系镣铐,锁簧轻啮犹不自知。
二
书斋里的灯火,总比窗外的月色要旧些。案头正摊着王汎森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毛细管”三字,总能莫名地使脊背渐渐生凉,原因无法说,自然也不是开着空调的缘故。书中言及康乾文字狱,非止刀笔明诛,更有暗噬之术。官府禁书令既下,文人便自发剜削藏书:钱谦益化作“蒙叟”“牧翁”的墨钉,屈大均成了“友人”二字,岭南陈恭尹更将奏疏信笺付之一炬。尤可怖者,乃顾亭林诗中“以韵目代字”的隐语,纵使三百年后学人执卷苦索,亦难尽解其幽曲心迹。这删削涂抹的功夫,何尝不是士人将刑具预先备在自家书房?刀锋未至颈项,手腕已自颤颤。
王汎森此书,并非描写廷杖、诏狱那般雷霆万钧的显性权力,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幽微、更为日常的所在。他所言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是一个精妙绝伦的譬喻:最高层的政治压力,犹如施加于一盆静水之上的巨力,这股力量并非直接倾覆整盆水,而是透过无数肉眼难见的毛细管道,如水分子般,一丝一丝地渗透到社会肌体的每一寸末梢,抵达书斋、私塾、宗祠,乃至文人“内心最隐秘的部分”。
这种渗透的机制,极为高明。它不全然依赖朝廷的明令与禁书,那只是冰山一角。更厉害的,是它成功地制造了一种“无边的氛围”,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看不见却人人自危的心理气压。在这种气压之下,透过普遍的“自我压抑”与“自我删篡”,规训得以完成。权力不再需要一个具体的执行者时时刻刻在场监控,因为它已经成功地将监控的种子植入了每个人的内心。
三
这便是王汎森为我们描摹的,一个在高度压力下,人人“以礼自绳”、层层自我设限的社会。权力的毛细管,最终流淌的不是养分,而是稀释了自由与元气的冰冷药剂。这使我无意中记起《笑傲江湖》这部书。《笑傲江湖》烟波浩渺,多少英雄豪杰、奸雄名士在权力的棋盘上起落浮沉,金庸说旨在“刻画中国三千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这句话恰好与王汎森的研究形成了惊人的互文。如果说王汎森描绘的是庙堂之下士人圈的规训,那么金庸则是在一个虚构的“江湖”之上,以武学为载体,淋漓演绎了这套权力游戏。
《笑傲江湖》的江湖,绝非一片自由放浪的乐土,而是一个结构森严、规训无处不在的权力场域。权力网络并非单系于东方不败红袖翻覆,却很像一片无形雾霭,罩在三山五岳的每一处亭台。权力运作精微幽深,尽显于空间规训、知识霸权与无形钳制之中。
华山派剑、气两宗的路线之争,五岳会盟座次排定,无一不是透过空间布局来强化等级与秩序。华山剑招,一板一眼,师父的教学之道,便是将徒儿的身体细分为可操练的单元,八股章法刻骨入髓方称正宗;《葵花宝典》更非寻常秘籍,实则是攫取终极权柄的“知识即权力”之关键枢纽。得之者便可号令群伦,重定武学纲常、江湖秩序。而所谓的名门正派,其本身就是一种知识霸权,他们划定“正”与“邪”的边界,将日月神教贬为“魔教”,正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合法性与统治地位;而日月神教的“三尸脑神丹”,堪称以药石行层级监视之绝唱,令恐惧内植心髓,纵无人督察,教众亦绝对服从,这正是毛细管权力最阴森的体现。
四
江湖对“正统”的偏执,对“魔教”的仇恨,都形成了一种“无边的氛围”。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为一切权力斗争、内部清洗和政治阴谋提供了天然的道德合法性。任何对这套话语的偏离,任何试图跨越正邪界线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对整个“正派”集体利益的背叛。
刘正风的“金盆洗手”,便是在这一语境下的一次“政治不正确”的行动。他渴望退出江湖纷争,回归田园琴酒,这在权力中心的眼中,是对五岳剑派对抗魔教这一集体目标的“拒不履行义务” 。他的个人追求与组织的宏大叙事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江湖,这个看似可以来去自由的地方,实际上并不允许其成员拥有真正的退出自由。
刘正风与曲洋的友谊,纯粹建立在对音乐的共同痴迷之上,是一种超越了身份、门派、正邪的灵魂共鸣。他们的琴箫合奏,是对自由与铁骨的咏叹,却不幸在一个充满了表演性、猜忌与“自我审查”的伪江湖中奏响。在权力编织的巨网之下,通过销毁承载自由精神的载体,完成对权力最彻底的屈服。即便是最终携任盈盈归隐的令狐冲,也是带着几分疲倦与无奈的逃离色彩,而非全然的胜利 。
琴箫虽在,但江湖已寂。
五
少年读金庸,只见峰巅孤松傲雪,眼珠子恨不得焊在主角身上;如今流光暗度,人间百味渐次翻腾,方悟松下有苔,石缝有草,蝼蚁衔土,万物皆在成全那座山。《笑傲江湖》的不戒和尚,正是江湖既清且浊的万千倒影里,真实存在的一个。在我看来,不戒和尚是一个深具哲学意蕴的符号。在王汎森所揭示的那个权力无孔不入、人人“自我审查”的微观世界里,不戒和尚以其彻底的“非功利性”和“非政治化”,成了一个刀枪不入的“绝缘体”。
《笑傲江湖》中,风清扬选择了避世的清醒,令狐冲追求着不可得的清醒,莫大先生则在悲凉的胡琴声中旁观着清醒。他们或出世,或挣扎,或忧愤,但都仍在权力的引力场内。唯有不戒和尚,他既不出世,也不挣扎,更不忧愤。他以一种浑不吝的、近乎于“耍无赖”的方式,生活在江湖之中,却又完全独立于江湖的评价体系之外。他不寻求推翻任何权力结构,因为在他眼中,那些结构本就虚妄如烟。
他一生行事,看似荒唐,实则只遵循一条内在的法则:至性与本真。他为爱妻而削发为僧,为爱女而奔走江湖。所有行止皆源自生命深处的灼热驱力,而非俗世规条或利害权衡。江湖上那套关于正邪、门户、辈分的毛细管网络,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可以渗透的缝隙。权力需要藉由人的欲望、恐惧、虚荣来发生作用,而不戒和尚的生命力是如此的饱满、纯粹,以至于权力根本无法与之对接。王汎森笔下的清代士人,核心行为是“自我删窜”与“自我压抑”。而不戒和尚的全部行为,恰恰是这两者的反面:彻底的自我表达与彻底的自我释放,在那个宏大叙事泛滥成灾的时代,却成了保存个体精神完整的唯一法门。
不戒和尚最具代表的杰作,莫过于创立“恒山别院”,堪称是对整个江湖权力结构的一次戏谑式解构。在那山高水远、烟霞自养之地,“恒山别院”兀自焕发着江湖本色,那是一片挣脱羁縻的离心力,野生的、丰茂的“化外生气”。这座小小院落,便似天开一角,容得下不拘绳墨的万物生机,它是刀光剑影里,一段自在自为的空谷足音。
六
想来,真正的“笑傲江湖”,原不在绝世武功,也非权斗胜出,更非遁世山野。它倒似那不戒和尚:于浊浪滔滔中,偏能凭自家章法、心头一点真,筑起一方权力染指不得、世故渗透不入的清净天地。他活得像个“笑话”,却让整个江湖都成了笑话。那真能解得《笑傲江湖》个中三昧的,恰是这灯火阑珊处的独行僧——刘正风与曲洋以命相酬谱就的绝响,终在此处觅得了真正的回音。原来浮浮沉沉的江湖寓言,终需一副不识时务的赤子心肠来点破。
江湖骇浪千重,唯此孤峰背影,自成一襟晚照。
2025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