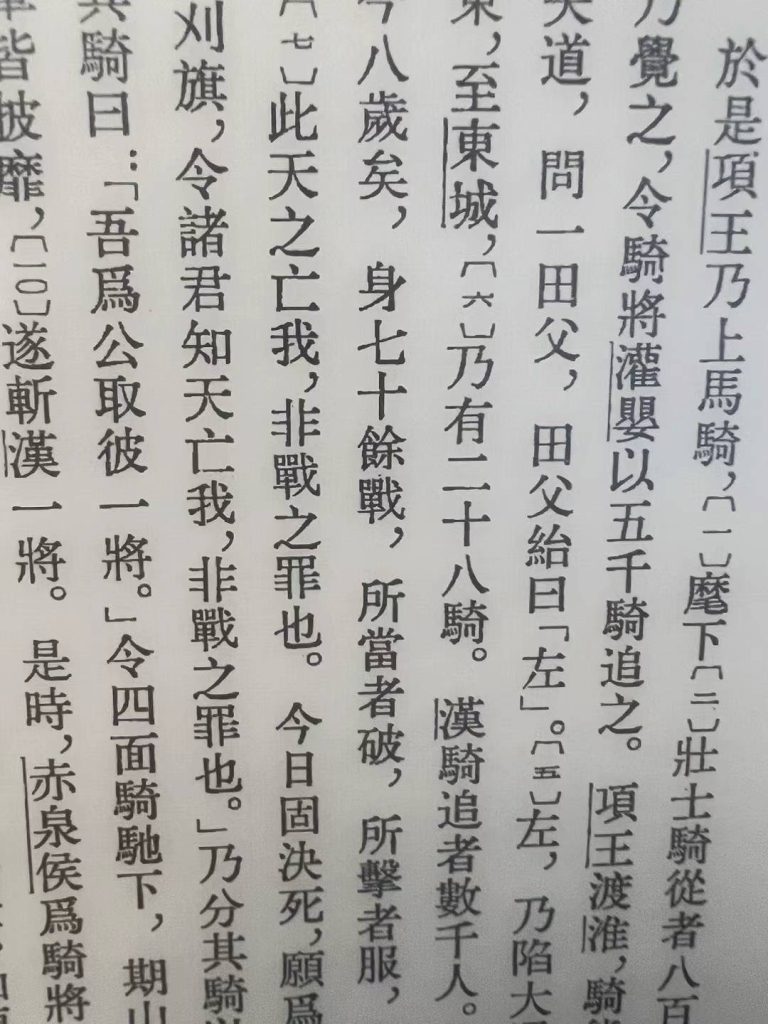《庄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商君书》: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庄子认为圣人与大盗为相伴而生的概念,若由圣人来建立规则,则大盗生矣。因此应道法自然,绝圣弃智。以民众的自发秩序,自能建立有序社会。既然圣人与大盗共生,那么圣人死,则大盗不存。
商鞅则持相反观点。在商鞅看来(以下仅转述商鞅观点,与本人观点无关),无论是任何社会,绝大多数民众是极为短视且肤浅的,每天便是发朋友圈吃吃喝喝醉生梦死。因此重大决策绝不可以交予庸众讨论,子产若是明智便该马上将乡校砸烂。
至于两种观点孰对孰错,当然,都是既对且错。对与错都是相对的抽象概念,宇宙空间中并不存在一个具体的有形的比如一块岩石形状的叫做“对”的事物。任何的表述和论断都会一定程度贴合现实但又必然失真。深刻相伴于肤浅,以及角度的千差万别,都是定然同时存在的。按照庄子的观点,一个社会根本不需要领导者,领导者只会相伴于破坏者,或者其本身便是破坏者。以每一个社会个体自身的创造力,自然会形成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但是建立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必然以多样性的群体为基石。如果所有个体都具备完全相同的特征,那么所形成的一定是一个毫无抗风险能力的不时即亡的社会。那么问题出现了:既然自然法则要求多样性,要求个体之间必须存在差异,则具备不同特征的个体在在同一社会形态下所得到的社会反馈是不同的,因此即便初始状态相同,也必然产生阶层的划分,终究,圣人出矣。既然自然界对多样性的需求必然会产生圣人出矣的结局,那么庄子的论断显然是有局限的,而且他只给出了绝圣弃智的建议,并未给出具体的操作方式。
对于产生“圣人”后如何消灭“圣人”,自然界非常灵活。气候与环境随时变化,在一种气候环境下演化出有利特征的物种在随时有可能在下一场气候变迁中因该特征与新环境不相适应而灭绝。人类社会没有自然界演化灵活,但也大同小异。比如一个人只会溜须拍马陪酒陪睡,那么其在一种社会形态下可能是情商高的典范从而跻身“圣人”行列,但是换到另一社会形态下则马上被边缘化。特征无所谓对错,演化需要而已。产生“圣人”是社会多样性的需要,而消灭“圣人”又是社会演化的必然结果。自然界一向是如此无情且仁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