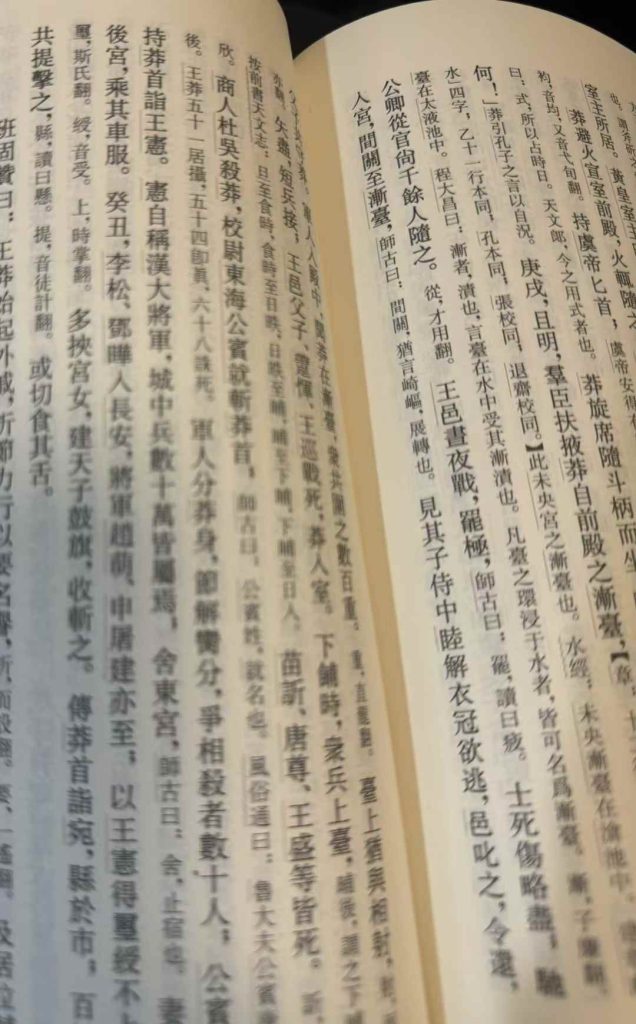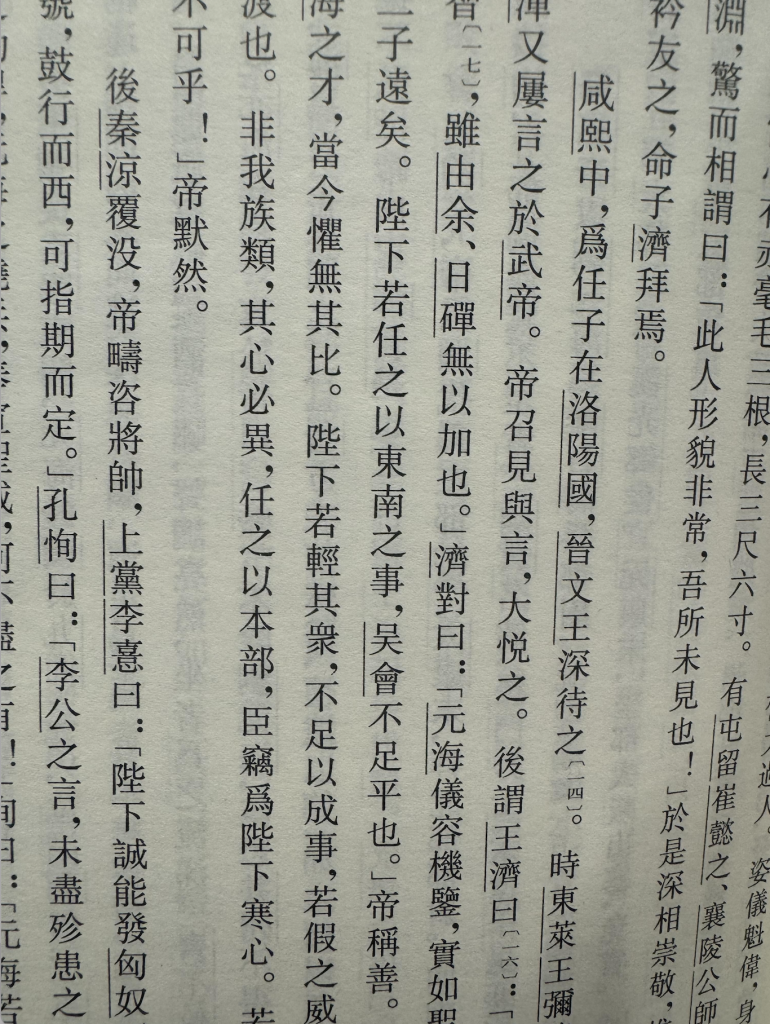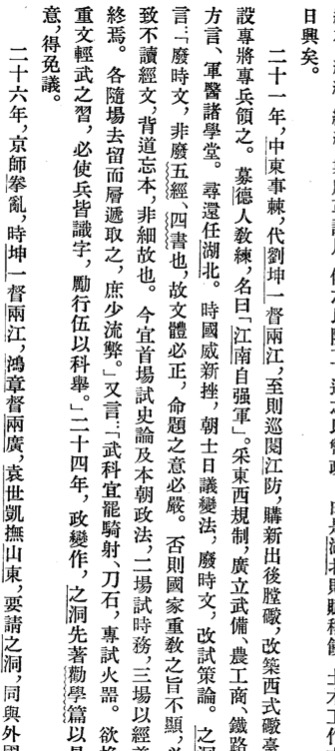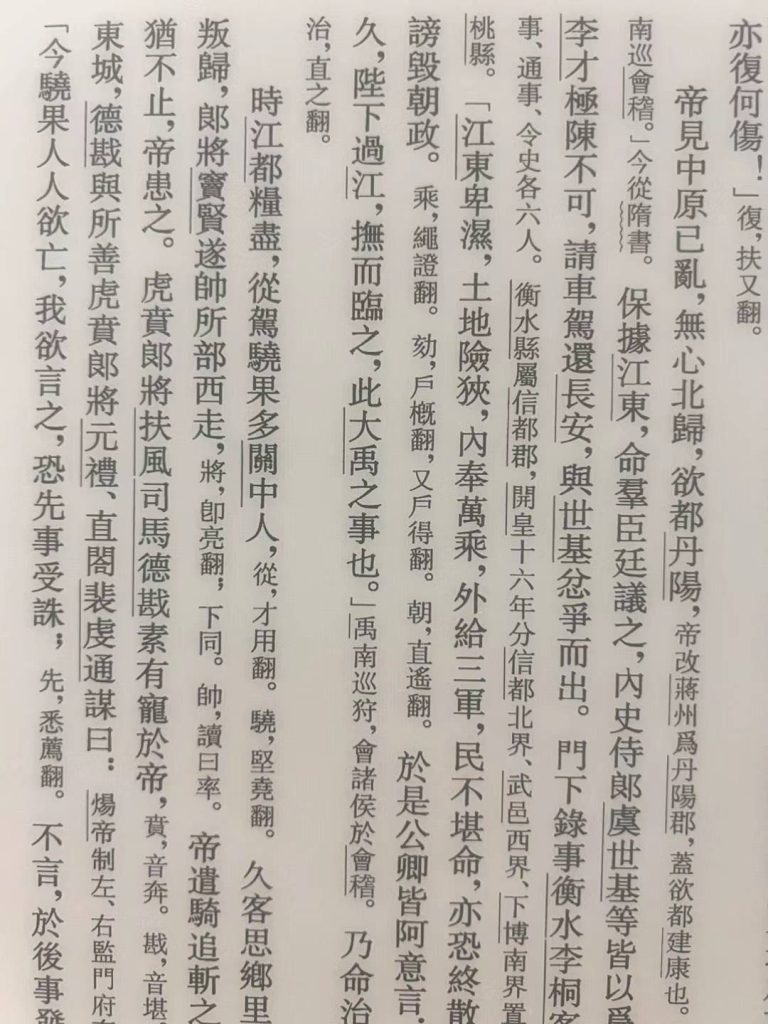王莽既然选择以和平过渡的方式全面接管前朝资源改朝换代,那么自然也要全盘接受西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带来的血流漂杵危局并危及自身。正如东汉末年的董卓,作为西北军阀,本可以同韩遂一样腾挪之余得以善终,然而被何进召进洛阳并面对虎狼环伺成为众矢之的,那便非死不可了。王莽或是垂涎帝位已久,或是被历史潮流裹挟而不得不为,抑或王莽自己也分不清二者之区别,总之王莽绝不会天真以为改变皇帝名姓便可以解决社会矛盾,井田改革便是王莽力推之作。无论是改革本身,还是与之配套的理论基础,即刘歆抑或王莽本人伪造的《周礼》,其可实施性都是存疑的,骤然实施,流民问题未必得到缓解,同时与官僚集团的对抗必定激起更大的矛盾。然而从更为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改革本身能否推进根本不重要,重新的利益分化已经势在必行。人类历史的每一次解决矛盾的变革当然会激起更大更深层的矛盾,这是宇宙物理学和哲学的基本要求,人类也正是这样走到今天的。王莽这等有理想有情怀的人,当然不可能因为困难而效仿秦二世坐以待毙。当时有人劝说王莽:“骤然改革,淘汰官吏,必然在底层官吏中涤荡出李自成,最终毁灭新朝。”王莽反诘到:“你对历史理解得如此浅薄草率,可见正如与我同姓的一位先生所说,学历史和学微积分学物理一样,是需要很高的门槛的,既要有数学和哲学为基础培养的逻辑思辨能力,又要有文言打下的语言功底。像听故事一样学历史,纯属浪费时间。李自成自己属于何种阶层哪种职业,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失地失业流民集团。如果放任冗员不加裁汰,那么只会在社会对立中培养出更多的流民人口,催生出更多的李自成,届时局面更加不可收拾。我拜托你不要人云亦云地肤浅理解历史。”王莽同董卓一样,在军事上失败后便不存在势力退潮回到一方军阀势力的可能,必须以自己以及整个集团的覆灭而收场。正如李斯死前所期望能够再“出东门、逐狡兔”一样,既然已经深度参与了利益对抗,便不能再作此奢望,这也是四世三公的袁绍所受的拖累与羁绊远高于孟德的根本原因。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