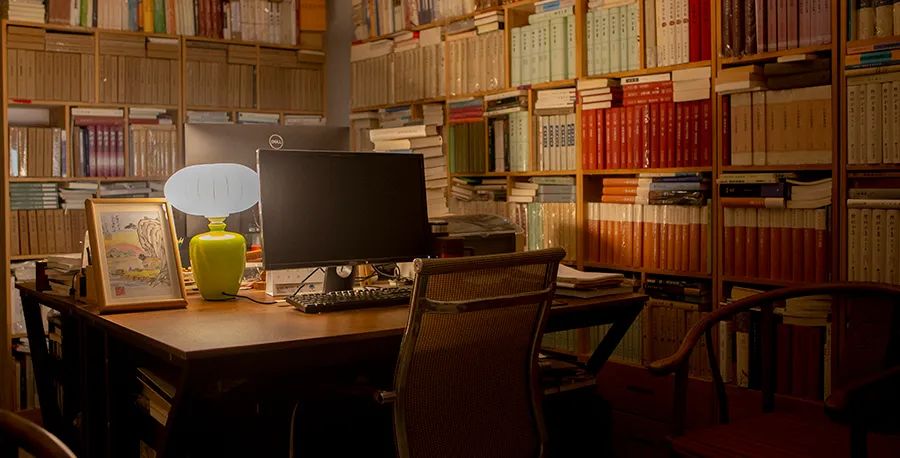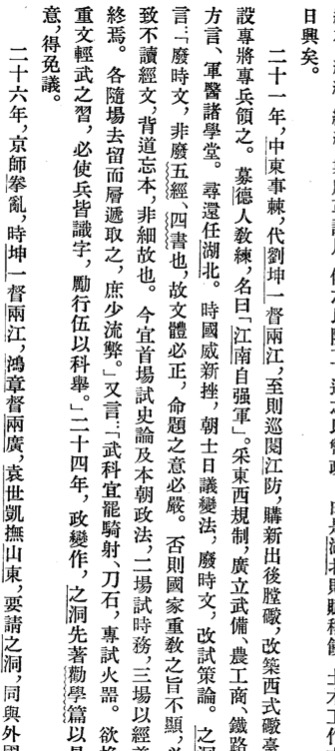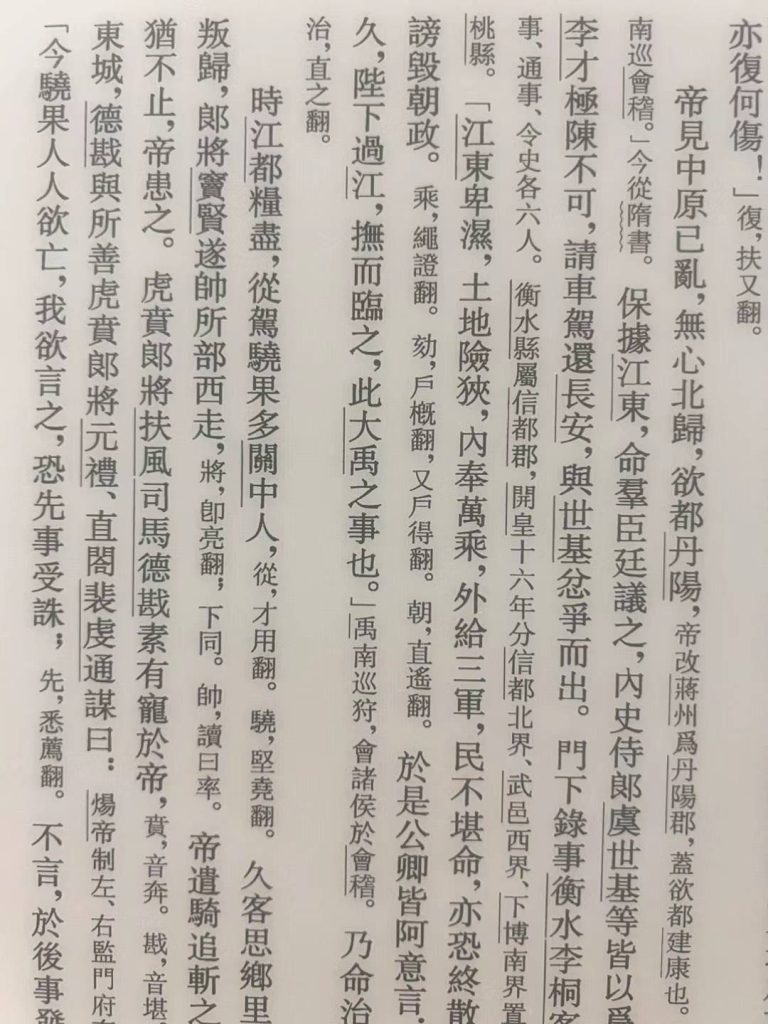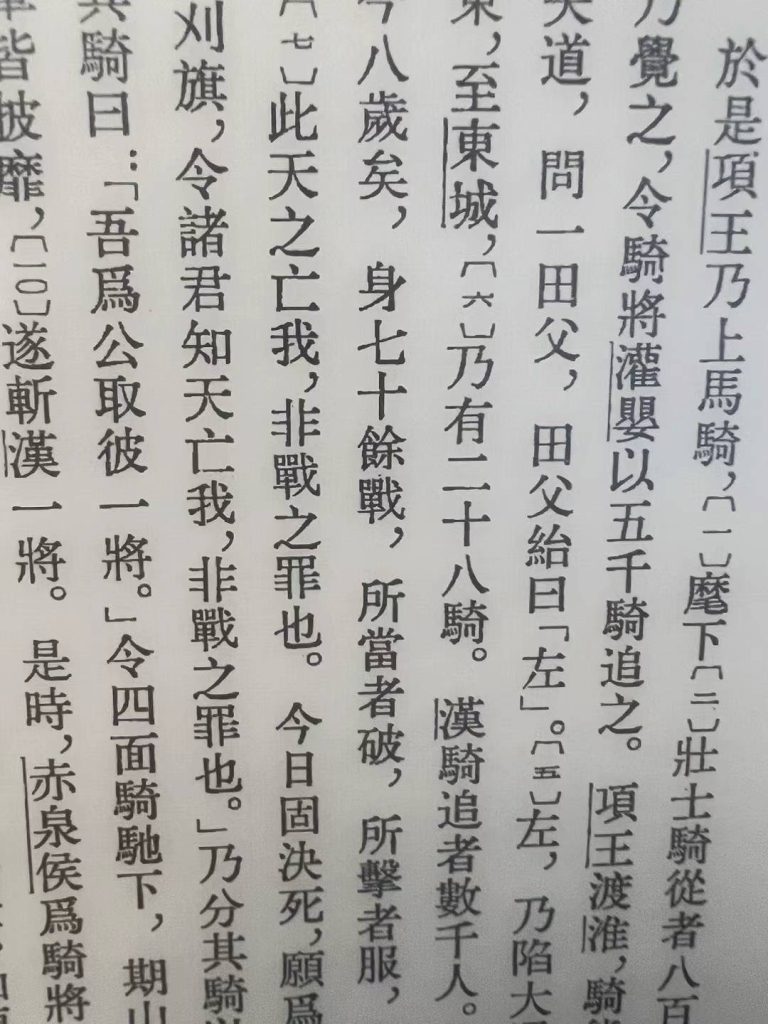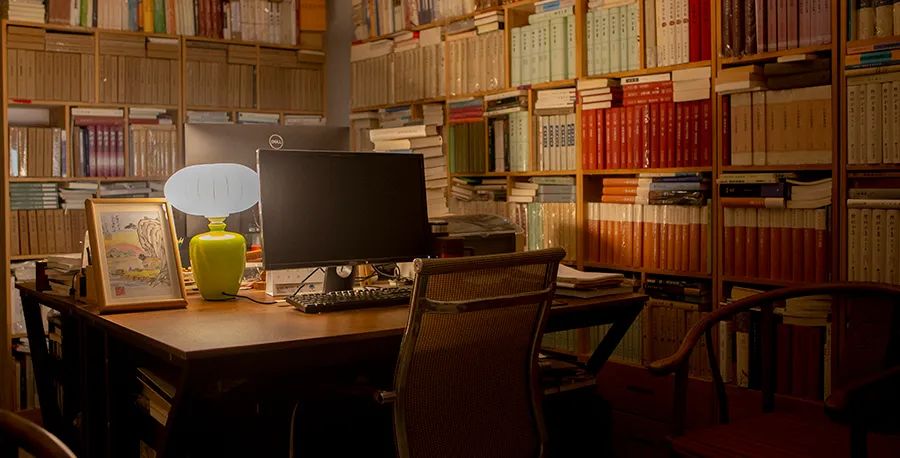
文 /江湖传说中帅得掉渣的笔帅
庚子至今,一晃四年。近城远山,都是人间。因此随意拣了几则,为了方便,省去日期,以数字代替。
一
晴。因积书盈柜,遂开柜理之,一书坠落,断为两半。吾视之,乃《蝶恋花》。呜呼,相伴一载,遽尔玉殒;或烟景似醉,恋恋红尘竟弃吾羽化乎?哽恸留联,奈何奈何。吾以胶水勉强粘之,每一念及,哀慼益深。
二
晛。回奥园修订集贤校本课程。午收《山谷词》,昨日购之。前言记载,1950年代,马兴荣受龙沐勋勉励,着手校订山谷词。中间事阻,一搁四十年。四十年后笺注已毕,而忍寒老人墓木已拱,诚如山谷道人“老尽少年心”也。
三
晴。晨继续修订集贤教材一事;友以生日书《牧斋集》见贻。忆及初见,当在两年前岁末,今予诚如牧斋之谓“头白那禁更白头”也。
四
晴。陈姓友人岁末来穗过访,为余校订汉服一书,感谢莫名。今远赴蜀地,再会之日未期。
五
晴。仨徒以《郑天挺日记》见贻。一代学人心路,刚毅坚卓之精神令吾辈心折。惜仨徒设计之路终为稻粱所屈。夜读平安帖,忆昔游兰亭,茂林修竹,清流潆洄,而逸少遗风,时时入梦。
六
晨阴。集贤第一册设计完毕,交付打样。收友人所贻生日书《蜜蜂的寓言》。即便杏花消息阑珊,而缅思旧雨如故,感切于心。黄昏冥晦,雨意浓密。戌时伴以轰雷,风疾雨骤。
七
晨阴,黄昏小雨。回奥园煮龙井,窗前小啜。不经意处扫视柜上裱框之枯叶,猝尔记起昨梦。裱框坠地,枯叶灰殒,余竟伤心不止。购《梅贻琦日记》,灯下读之,为运转学校而周旋于政客,奔波四方,忾叹经济不易。
八
晨雨丝如织。报纸如期出版,差一司机运送,或烟雾迷蒙,竟兜转于途。午寄集贤课程。购《贾伯斯传》,人生浮云苍狗耳,当听命于内心。
九
阴雨似秋。敲定《馨笺集》版式。去年今日,收绍兴佳酿若干。晚于302清检物事,忆昔共共谋前程,美醖香茗;而今泊港避浪,怀想依依。
十
寒雨不止。清明假日。晨十时起身。午饭煮面,吃毕继续睡。17时醒,又闻窗外雨声淅沥,清寒透幔。夜读《梅贻琦日记》。“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何止为政?人生于世,口只为吃饭也。
十一
阴雨连绵。午与小徒国豪茶聊颇久。渠言设计终非所好,拟改辙动漫。予嘉善,少年不废光阴,桑弧蓬矢,丈夫之志,追随内心,佳矣。
十二
晴。收《馨笺集》样书,并寄往京城。封面质量有所欠缺。午与彭总合力将《正是读书时》挂于墙上。读书四时皆宜,所谓“落花水面”“小斋幽敞”也,而读书亦误己多矣。着手集贤课程第二册。
十三
晴。购《情人》。道乾先生译笔干净流丽,上等文本。而杜氏之爱,亦乖逆而沧桑。以《王羲之墨迹》赠晋桃兄,羲之书自不必言,而才情冠绝,数言传其意。
十四
晴热。着单衣依然汗湿。欲更新源流公众号之汉服杂志书,茫无头绪。晚翻《江村经济》。中国农村的问题是饥饿问题。
十五
晛。源流公号推送完毕。字字不易。现下中国,以至更长一段时间,做“文化”尚嫌寂寞。予之文案“灾难之下的文化逆行”,语过乐观,其实质是“文化之烈士”也。收《Life Wear》杂志,乃设计之反面教材。夜落小雨,即停。
十六
《梅贻琦日记》断续阅毕,累时月余。予随其足迹,一路风尘,而今终点已达,心生几许怅然。梅氏治校兼涵并容,始终坚持学术思想自由。反观今日,既无思想,且多高楼。斯人不出,如苍生何。夜雨即过。
十七
晴。与大龙互校《馨笺集》,折腾一日。识字忧患始,信然。大半光阴葬此,生计艰难。
十八
“5•1”依旧劳作。圣经云,人类终身劳苦,方能得食。众生不易。收香港三联版《彷徨》以及三民书局《桃花扇》。夜读吕纬甫,琐碎之日常,悲怆之磊落,一股愤懑抑止不住。理发。发如霜,已侵半边青丝。
十九
晴。友人发来汉服推广之订阅号,承其校订,寸衷感戢。纸质凋零,电子盛行,昔日本木下氏制作两期《Life Wear》令纸质杂志起死为生,予之汉家一书当再令纸媒复活N次。晚收敦煌版《坛经》,其版本众多,总难逃去不下怜世心肠,寄之以贝叶。
二十
晴。拟汉语江湖丛书合同。《后浪》刷屏,虽陈词慷慨,却空洞做作,自慰自欺,世道往复,卑劣与愚蠢依旧轮回不息。前浪、后浪不过一泡沫耳。购港版《呐喊》一册。五四以后,铁屋依然完好。
二一
晴。始着短袖。《馨笺集》二稿寄京。前后逾月有余。所谓有志于此,遂经磨砺,不足宽慰一二矣。灯下校稿,郁燠难耐,子时就寝。购《汪兆镛诗词》一册,前朝番禺遗老,执拗保守,却心忧黎元。与汪兆铭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二二
晴。晨读。予谓人于天地,须留三分市侩,处世不致扞格;须留七分耿介,谋生当图踏实。收《嬾真子录》《松窗杂录》各一册。正史无可观,惟稗官消夏。时至黄昏,黑云覆压,闷雷隐现。俄尔风疾雨骤,列缺霹雳,丘峦崩摧。
二三
晛。午收《毛泽东早期文稿》,其中《体育之研究》有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于今观之,远离甚焉。不特雄性如雌,其精神亦多残疾。
二四
晴。编集贤课程。收台版王鼎钧散文集。乡愁郁勃难遣,积于左心房。半生漂泊,他乡难置灵魂,故乡难置肉身,总归如此。日夕天黑似墨,继而雨挟风势,窗外瞬间海景。
二五
昙。外出,午归。收港版《呼兰河传》一册。萧红叙事寂寞,落纸成烟霞,宛然普鲁斯特之注脚。楠木发来日签,以丰子恺画配图。丰氏只生欢喜,片片落英,都沁着人间情味,究竟情因年少,酒因境多。
二六
晴。熙阳遍照。购台版《西厢记》一册,陈之几案,日夕相晤,挽文思之枯涩。雠校《馨笺集》,即付剞劂,叹成书匪易。向晚云厚日敛,窗外淅淅飒飒,顷刻狞雷驱猛雨。挑灯读金瓶梅,惜太监版,不尽人意。
二七
礼拜。赴奥园校勘《馨笺集》。收《元曲纪事》《王羲之尺牍集》各一册。夕景昏霭,瞬息惊电裂空,雨泻如注。挑灯读右军帖,如聆松风,浣尽十年尘胃矣。逸少任诞之士,写字乃末技耳,今人追捧如此,亦可笑复可叹。
二八
晨雨如丝。收《儒林公议》一册,初夏读宋人笔记,颇能消暑。晚天沉,少顷色霁。挑灯《秋灯琐忆》,芭蕉夜雨,点点滴滴而已。
二九
连雨多日,今霁。“汉语江湖”诗丛合同拟毕。收《逸梅闲话》一册,偏三国之故实。三国风云激荡,人才辈出,无非功成骨枯,家天下耳。窗外月出,夏月宜枕簟,暂不读书,烹茗自娱。
三十
阴。午梁兄来,商计图书出版一事。集贤课程第二册编讫,三稿《馨笺集》寄京。收台版王鼎钧《风雨阴晴》一册,桑田几变,所谓故乡,无非亲人具在。窗外淅冽冽,挑灯风雨阴晴。
三一
阴。收全唐诗,大略性情所寄,千载同符。傍晚雨横,回途雨势再增。挑灯唐诗,信手732卷之长屋,文字足感,不惜身命。
三二
同事约酒,惜因事未果。雨令夜长,挑灯《幽梦影》,美学读物,有小迂腐而无酸腐。
三三
昙。晨拟出版合同。收《醉古堂剑扫》一册。此书著者假托眉公之名,可知古代书商亦借名人效应,以资速售耳。午未寝,手书几行寄友,不过寒温之句。薄暮行云叆叇,夜间轰雷不止。挑灯醉古堂,虽为清言,亦道人性曲尽岩险。
三四
昙。《三轻整脊》款项已收。过午芳姐见访。茶叙忻畅,书之后期,需要渠道,方能成事。所言颇中肯。其诗集《戴口罩的春天》遂敲定托予出版。庚子大疫,神州遭劫,诗人本弱,下笔千钧,呐喊,讴歌,彷徨,批判,百感郁勃,发而为诗,启瞶振聋。镜不幸而遇嫫母,砚不幸而遇俗子,剑不幸而遇庸将,此书幸而遇我。
三五
阴。芳姐发来诗稿《戴口罩的春天》。傍晚见午饭残留,遂加热食之。夜间归途,抬头见月。挑灯全唐诗,见则天叙次第五卷,与长孙皇后、上官婉儿并坐。终究后妃矣。
三六
阴。夜过石四。诸多念念,不得停住。收《楞严经》一册。忆儿时明真,虽未开蒙,亦可辨色,而今经教化,却混淆黑白。一度憧憬成人世界,及长,却未能成为孩孺时所想之人。挑灯读经,时光流易,性未曾皱。
三七
霖沥。收《王韬诗集》《西学东渐记》各一册。晚至超市购日用品,归途无雨。夜挑灯兰卿、容闳。同属睁眼看世界之巨子,各有各命途。
三八
昙。《馨笺集》出版,500册装箱寄京。十旬竣工,期间辛艰,自知而矣。今重负已释,眼笑眉舒。
三九
晴。客户来。一时雅论清谈,啜茗舒畅。申时赴根聚地,席间饮桃花醉,盖量浅,羞于举白。戌时归,洗漱毕阅《松坡文集》,语不妄发,多有为之言,亦可破孤闷。
四十
“鹦鹉”绕道,带雨不止。惊悉常州市河滨小学之缪可馨坠楼事件。原来作文杀人见血,于今见之,原来看客之幽魂,人间尤夥。默哀。《馨笺集》已到京。京城疫情复燃,大龙再遭禁足,几箱书籍暂置保安室。大龙未能亲抚书皮亲闻墨香,焦炙不已。
四一
晴。芳姐来,商洽诗集出版并封面设计事宜。收《莫友芝全集》。疫情所致,半年未置大部头,令伯涵京华一见倾心者,不多,当不吝购得。午阿豪来辞行,随身两年,今会见未期,徒增感怆。
四二
晴。收《全元散曲》三册。元代国力,自是无法比之与唐宋,元散曲自然生存匪易,甚而自生自灭,留存数量不及唐宋诗词之三分一。书册侵食地盘严重,复理之,有迅翁“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之笑叹。
四三
晴。打点行装归家,父母早早候于门扉。夜闲话,母亲为予手工针织一件毛衫,今已完竣,令予试着,贴身舒适,伊开颜。予瞥见伊素发稠矣。更深回房就寝,逡巡于书柜良久,信手打开狄金森。
四四
晴。晨别家赴穗。父母养一肥鸡,杀之,命予带便置于行装,端午加餐。谋生江湖,萍踪浪影,未得伏侍左右,亦是罪愆。午时到奥园,收熊教授潢裱 。申时日环食,端EOS6D摄一帧。夜挑灯高季迪诗,有“月明林下美人来”一句,季迪为伟人欣赏,亦由此句。予独喜《龙城录》,乃忆大梅花树下。
四五
晴。“汉语江湖”诗丛选题上报,撰丛书之简介,250余字。收《苌楚斋随笔》两册。夜挑灯刘十枝,逸事可观,多补正史之阙。论诗则主张“全以意胜,不在词藻”,“词藻”易,“意胜”须天授欤?
四六
晴。芜湖宋磊赠予一册《一心惟尔》,书名佳,书评亦可观。收王鼎钧《小而美散文》一册。夜挑灯小船小桥小渡头,细雨临风岸,皆各有因缘。
四七
晴。夜于胡桃里饮酒,不佳。归寓后洗漱,似昏而醒。凌晨二时未眠,读王塘南集。偶瞟手机,得悉迭戈逝世。场下糜烂,场上封神;半个迭戈,已然称王。
四八
晴。冻。收包裹一件,芜湖寄出,乃《西湖游览志余》一册;得大龙所贻书籍若干,《说园》一册,《馨笺集》一册,《笑傲》一册,并嘱予在其扉页互签,以志之。
四九
冻。风甚壮。题《馨笺集》打油一首:“一纸承诺十六年,午夜梦回忆从前。校得书中几个字,换壶清酒花间眠。”题《笑傲江湖》扉页一段:“此版笑傲封面竟UV烫黑金,且前插几幅彩页。稀奇。读笑傲宜干烈酒,快马美人俱往矣,惟一樽一曲,能诉衷肠,能知情浓,能慰平生。”晚收同事所赠《凛冬将至》,此夜沐手焚香,拥衾读之,心上温暖。
五十
晴。向晚离穗赴紫城,亥时下榻维也纳。卸下背包,拿出一卷《陶庵梦忆》。洗漱完毕,就灯翻阅,念其故国之思。尔后枕梦忆入梦忆。
五一
雾雨。晨七时起,驱车往乡镇一中学。其间与校长拉谈,彼谓办学宗旨,无他,唯“读书”尔。古今名著,灿若星辰,若不苦读,来校何为?终耗光阴。一乡镇校长,胸中见识,竟大不同,予为之悦服。夜饮大醉,子时抵穗。
END